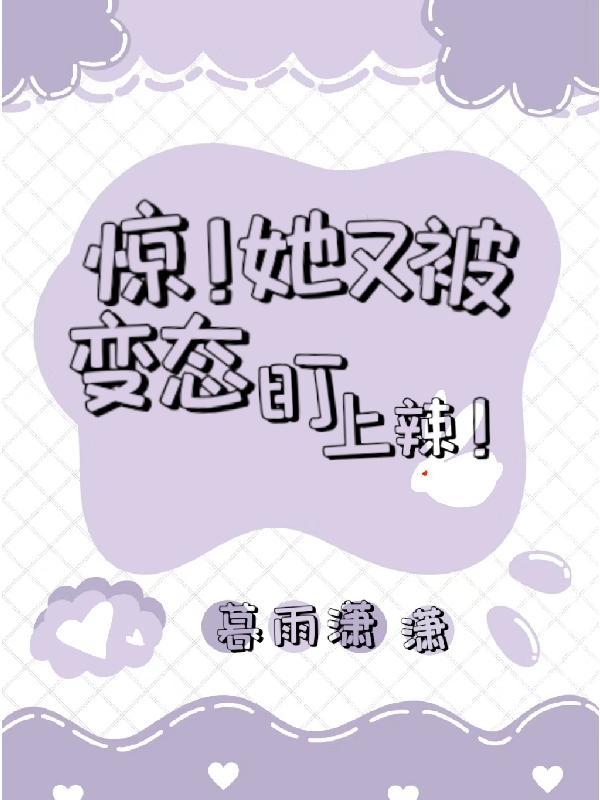笔趣小说>醉金盏全文TXT > 第200章 你能有今天靠的是谁(第2页)
第200章 你能有今天靠的是谁(第2页)
近几年的事模模糊糊的,反倒是早年的记得清楚。
我总觉得你们都还是小孩子,口味性子全是那时候的样,怎么时间就这么快呢,啊?”
往日,母亲这般说话,应聆想到她这辈子生儿育女的不容易,也就左耳进右耳出,不管了,可今儿着实火气大着,毫不遮掩地朝天翻了个白眼。
“五个女儿,三个儿子,”应聆道,“虽说家里不愁吃穿、有奶娘嬷嬷们分担辛劳,但您这辈子的确也吃了苦了。
我说您呐,既然年纪大了这不行那不行的,就好好在府里修身养性、含饴弄孙吧。
别操心些不该您操心的,尤其是别管我那几个姐姐。
她们自己日子过得一团乱,还三五不时回娘家跟您哭。
要不怎么说‘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呢?’跟您哭能哭出东西来,才一个个兴风作浪!”
文寿伯夫人脸上一阵红一阵白:“怎么说你姐姐的?都是为了家里人好,兄弟姐妹们互相帮衬,外嫁女才多有底气,你不能……”
“谁帮衬谁?”应聆指着自己,“从头到尾,是我这个最小的妹妹、做皇子妃的人,帮衬了所有人!”
文寿伯夫人反问道:“难道不应该吗?小时候是他们帮助你,现在换你帮助他们,一家人分那么细做什么?”
应聆正要驳回去,边上嬷嬷轻轻碰了碰她的肩膀。
“时辰不早了,等下殿下回来……”嬷嬷附耳劝她。
五皇子为人讲究礼数,若看到妻子与岳母吵翻了,恐是不大好。
应聆一想到这个,只得用力攥了下掌心,把冒腾的火气压住,瓮声瓮气道:“您不是来说陆念母女的事的吗?”
“是了,你别理睬那母女,”台阶给了,文寿伯夫人顺势而下,又不忘表达自己,“我也好,你哥哥姐姐们也罢,我们都是自己人,不会害你,谁知道外人打的什么坏主意呢!”
应聆咬牙道:“与她们走得近,那是殿下的意思,我难道要对殿下阳奉阴违?”
文寿伯夫人闻言一愣,又狐疑地看着女儿,摆明了不怎么相信。
应聆最受不了她这般质疑,蹭地站起来:“您难道真的孤陋寡闻到,不清楚郡王是广客来的常客?
王爷名义上是表弟,但内里的事儿满京城都心知肚明,陆念那女儿要真嫁了王爷,与我就是妯娌了。
我回头见了陆念、我还小一辈了呢!
殿下要与弟弟和极有可能的弟妹交好,我难道要拖他后腿?
你们疯了,还是我疯了?
您先看看我那九弟妹,人家是亲姐妹上阵和余如薇吃茶耍玩逛园子。
我这儿呢,我的姐姐们别说帮我了,还在想着办法拆台。
跑来说什么让我别和陆念母女往来,这是我能挑三拣四的事儿?这是您和姐姐们能指手画脚的事儿?!”
突如其来的质问让文寿伯夫人呆住了。
她何时听小女儿这么不留情面说话?
或许早年间有过,但自从应聆长大了、尤其是嫁入皇家之后,一言一行讲求得体规矩,绝不会这么和她说话了。
“你是翅膀硬了?”文寿伯夫人捂着胸口,难以置信道,“我一心为了你,你却说我是指手画脚?我们全家上下、拼命托举出来一位皇子妃,你却嫌弃我们……”
“拼命托举?”应聆笑容悲愤,“您指什么?您指我十二三岁时,骄纵到蛮横,自我又爱出风头,不合群又非得往群里凑的那些名声?你们的确费尽心思,才把那些坏名声洗掉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