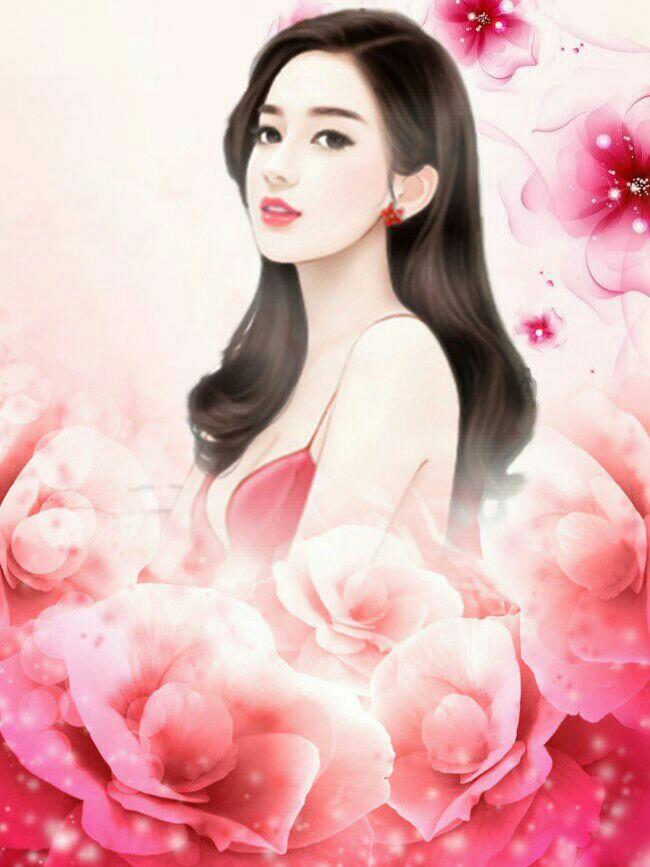笔趣小说>藏青果喉片的功效与作用 > 分卷阅读96(第1页)
分卷阅读96(第1页)
嘈杂细小的抖动声。我躺在地上,背部直接感受着水泥的冰凉。双手被反绑着,粗绳,越挣越紧。一个男人在不远处哼歌,曲调断断续续。我微微撑起身子,想看清他的样子。空间内唯一一盏明灯吊在他的头顶,照出他的眉眼。
我眯着眼睛认了半天,才认清这个人究竟是谁。
是徐言宙。他一副医生进手术室的打扮,全副武装。他一边哼歌,一边在桌面上码好手头的各类刀具。他很熟练,有工具,有空间,他甚至在我身下铺了东西。
他要杀我。
我感觉自己的脑袋在嗡嗡作响,说不清是精神太紧绷,还是被车撞留下的后遗症。悄悄环视四周,是一间没什么装修的密室,没有窗户,不算大。大概是地下室之类的。
我不是没经历过这种处境,负伤,无法联系外界,面对一个危险且可怖的男人。只不过上一个加害者更倾心于和我演过家家游戏,这一个则是铁了心要送我去走黄泉路。不管哪一个,都让我吃尽了苦头。
我扶着墙坐起来,默默地观察着徐言宙。一个家境殷实的医生,长得不错,工作也体面,比起年轻时声名狼藉的张明生,他收到的唯一恶评,或许也只有李译一句无心的闲话。这样一个人走在街上,谁会相信他会对自己曾经的伴侣屡施暴行,甚至痛下杀手。
他甚至替我包扎了伤口。看着腿上的固定绷带,我背后直冷汗。替我治伤,又要将我大卸八块。我不禁开始反思,我为人做事究竟出了什么纰漏,才会引得变态频频出现在我身边。我并不想自责,倘若能逃出升天,我还是会为自己扮演上帝,拨开眼前的云,往这几十年人生里望一望。看看究竟是自己太倒霉,还是偏执的人有相似的围捕目标。
“睡得好吗?”徐言宙讲话轻盈,似乎十分镇定,但只要仔细听,就听得出他尾音的颤抖。能嗅出精神濒临失控的疯癫味道。
我依旧看着他,没有回答。
看他这个状态,我逃生的机会即使有,也一定会很艰险。
“我从来没见过你睡着的样子,因为你始终不肯同我太亲近,”徐言宙朝我笑了一下,随手拿起一把匕,绕过桌子,慢慢走向我,“可我是你第一任男朋友,你亲口讲给我的。”
他越走越近,最后直接蹲在了我的身前,刀尖在我腹部比划,顺着衣服往上滑,他抬起眼皮,眼中没有笑意,只有失控,他说:“为什么你不依赖我?阿潮,为什么你要跟我分手,你看不起我吗?”
我眼看着刀尖像银色的蛇头一般,在我的身上巡行,下意识收紧了小腹,挺直脊背,想离它远一些。
但徐言宙一把捞住了我,不许我离开,他突然爆,朝我怒吼:“还是说,你根本就是骗我的!”
他有些神经质地凑了上来,似乎在嗅我身上的味道,轻声道:“你给几个男人睡过,你是不是已经万人骑了。”
我不敢出声,生怕一句话就激怒他,勉力镇静,只用眼睛看着他。
“你跟那个姓张的人走得很近,我知道,他很有钱,你是警察,你为什么要靠近有钱人呢?”徐言宙忽然又放低声音,装出一副苦口婆心的样子,“有钱人都很坏的,他们在外面三妻四妾,根本不可能对你忠诚,你也知道,我们的圈子很乱的。”
见我还是没有开口,他一把抓住了我的脸颊,硬摆正我的头,问:“我在向你讲话,阿潮,你听见没有。”
我看着他的瞳孔,与他对视了几秒,终于慢慢地点了点头。
“骗我!”他大力掌掴下来,打得我头晕眼花,嘴角渗出腥咸的血,一下子摔在了地上。
我眨了眨眼,想让自己清醒。
徐言宙已经站了起来,他居高临下地看着我,冷漠地说:“你也是骗子,你背叛了我,你自愿去做有钱人的玩物,也不愿意被我珍惜,你真的是自甘下贱。”
刚那一下使我牵动了身上的其他伤口,我咬着牙,挣扎着坐了起来。他的疯话听起来像不入流的小说台词,充斥着强烈的感情,好像整个世界都背叛了他。听了并不觉得可怖,反而觉得好笑。
我叹了口气,无奈地讲:“我同他没关系的。。。。。。”
“没关系,”他打断了我,慢慢走回桌前,说,“就算你背叛我,我也依然愿意对你好,我就是这样一个人,我恨不得自己是你的爸爸,能从你小时就开始保护你的一生。这世界上根本没有人比我对你更好,你为什么不知足。”
“保护?”不知是不是真的死到临头,我竟然没那么怕了。我笑着,头上的血还在流,划过眼睛时渗进了一些。
“没有忠诚,没有廉耻,没有对感情的纯粹追求,”徐言宙为自己带上了手套,他说,“我会为你结束这么低贱的一生。”
目睹我的死刑时间一点点靠近,我没再讲话,只留他一个人低声絮语。
“我不会让你疼,阿潮,你是我这些年最喜欢的,也是最舍不得的,”他拎起一把锤子,看了半晌,摇了摇头,“我不会让你疼,我不会让你和我爸爸妈妈一样疼。”
随后,他又拿起一把斧头,像上次那样观察,喃喃道:“这个,也不好,你跟那个贱货不一样,他过得太好了,比我好,更比你好,他活该血肉模糊,”
他已经杀过人了,我不是第一个。
我在心里咒骂他,骂了几个词后就想不出更多,听他话里的意思,他的双亲恐怕早已死在他的锤子下,我再诅咒也没什么用。都是可怜人,我连忙刹车。
“你看我多喜欢你,”他转过来看我,“对你,我总是下不了手,一而再再而三的心软。”
他不断标榜自己,自恋到极点。
杀人自然是要一次比一次谨慎的,手里的人命累积,自然不能让新的露出马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