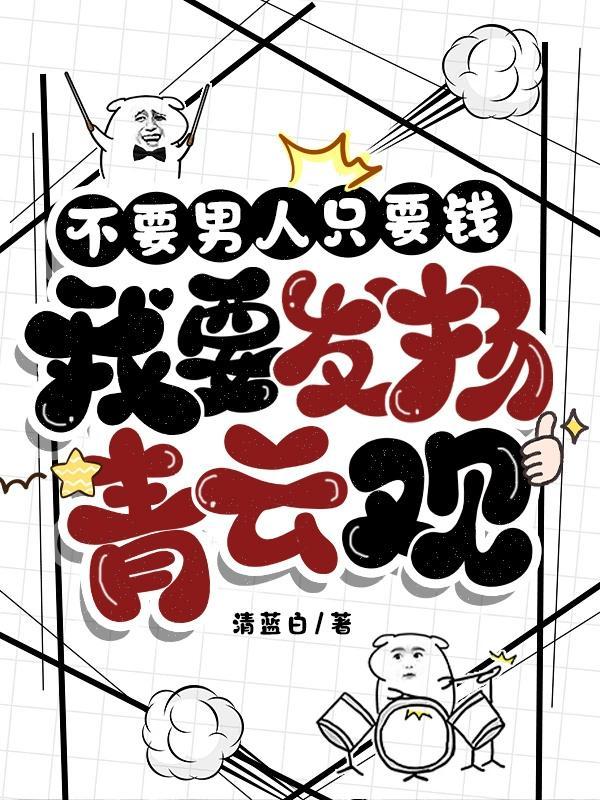笔趣小说>月明朝汐无弹窗全文 > 第73节(第1页)
第73节(第1页)
阮朝汐哑然把长卷往回拉,露出了颍川陈氏的五郎。
荀莺初捂了脸,迭声道,“陈五郎我去年才见过。确实高才,确实貌陋。这页跳过去跳过去!”
阮朝汐把长卷又往前拉,这回露出了钟十二郎。
荀莺初:“……”
两人把名册从前到后仔细查看了一遍,钟家儿郎在名册里的,只有钟十郎,十一郎和十二郎三个。
十一郎今年十八岁,性情开朗好动,喜爱呼朋引伴出游,荀莺初更看不上。
她起身把名册卷起,收去旁边,趴在桌案上生闷气。
“三兄偏心!他搅合了你和九郎的议亲事,却不愿搭理我和钟家的议亲事。”
阮朝汐心想,偏心?他哪里是偏心,分明是藏了私心。
但好友在她面前红着眼眶。她仔细想了一会儿。
“白日里你进书房,究竟如何说的?你不要和他大喊大闹,他惯常吃软不吃硬,越是吵闹他越是无动于衷。你不声不响地坐在他面前,落几滴泪,等他留意了,再有理有据地好好说。”
“你早和我说过好几次了,”荀七娘气苦说,“道理我都知道,但我做不来!”
阮朝汐极耐心地和她说,“事关你的人生大事,急躁不得。再做不来,也得沉下心思,忍着脾气,哪怕装着做,也得装起来。他见惯了你发脾气,你发脾气对他无用,非得你装出伤心欲绝、不吃不喝,连话也懒得说,人也懒得动的模样,他才会留意多看你,心里多为你思量几遍。”
她托起荀莺初俏丽的脸,仔细打量她此刻双目红肿,无精打采的模样。
顾虑地看一眼耳房那边,她附耳过去轻声说,“就是现在这个样子,熬两三个晚上少睡,熬到两眼无神,眼下黑青,气色不大好了,再坐在庭院里无声无息地哭。”
荀莺初原本还抽噎着想哭,听到最后倒撑不住笑了。
“听得像索命的女鬼。三兄见了要绕着我走。”
她这边破涕为笑,阮朝汐也弯了弯眼睛。
荀莺初叹气说,“都斥责我挑剔。其实我挑什么呢。比我大三四岁、五六岁,性情温和沉稳,可以包容我发脾气的郎君,豫州里必定不少,但定好了钟家……钟家哪有这样的。”
抱怨归抱怨,毕竟不像刚才进来时那么气色凄凉了,荀莺初开始摆弄书案上的羊脂玉笔山,把笔山上的几支紫毫翻过来覆过去打量,悄声问,“哪几支是三兄自己制的笔?”
阮朝汐并不看那些笔,头扭去旁边。荀莺初未察觉她的异样,在灯下仔细地摸索笔杆,寻找钤印。
原来书案上每支都是。
荀莺初翻出两张大纸,在纸张上试笔尖柔韧硬度,写得正是个“钟”字。
看到那个钟字,阮朝汐便想起了钟少白。
护送她前往豫北,半路混乱中途,意外被重物砸伤骨裂。即使这样,他也未责备抱怨她什么。
荀莺初和钟少白一个性情急,一个脾气硬,两人脾性不投,当着她的面争吵不休。阮朝汐心里默想,或许是两人自小一起长大,太相熟了,以至于看不到彼此的长处,只看到弱点。
“钟十二郎虽然性情不够稳重,学识谈不上高才,但他人品极好,是有情有义之人。”阮朝汐的指尖停留在“钟”字上,轻声道,
“毕竟有从小的情谊在。今日你来了,我听说十二郎以后就要天天关在南苑里,实在可怜。我想和你一起去和荀三兄求情,叫他把十二郎放出来,可以在庭院里走动。你觉得呢。”
荀莺初一口应下,“本来也不是我要关他的。明日我和你一起来书房见三兄,把十二郎放出来。”
阮朝汐微微地笑了笑,心里的牵挂放下几分。
荀莺初试够了笔,重新把名册拿在手里细阅点评,和身边好友嘀嘀咕咕。
“不能只我一个跟你说。阿般,你心目里的郎君,可要求高才?”
阮朝汐瞬间想起了满腹经纶、强拉着她品评诗文集的荀九郎,失笑摇头。“不必高才。我和高才谈不拢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