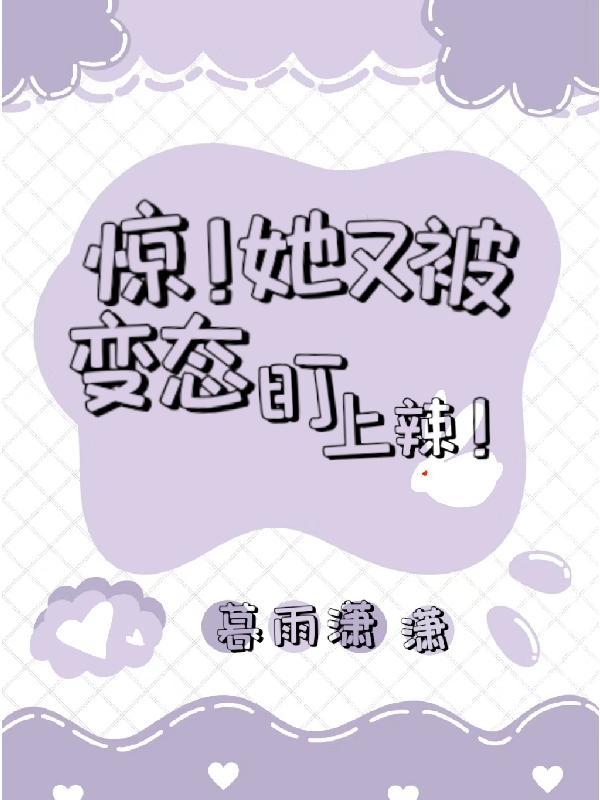笔趣小说>吞海archive > 第17章(第1页)
第17章(第1页)
只尴尬了一瞬,步重华先发制人:“你平时都在这儿?”
“对。”吴雩咬着烟,手指轻轻敲着酒杯,漫不经心地带着股混不吝的气质,“我还是这儿头牌。”
步重华呛着了,啤酒顺着鼻子喷出来,火辣辣的酸爽。
吴雩有些嫌弃地递给他纸巾,补刀:“第一次点人?”
“点什麽?”
“点人啊,”吴雩掐灭烟,抿了口酒,揶揄道:“咱是邻居,近水楼台先得月,我给你99折。”
远处五颜六色的光时不时扫过吴雩似有若无含笑的脸庞,摄人心魄的好看。步重华掩饰性地别开目光,随口接道:“那你一晚多少钱?”
吴雩拍着桌子大笑起来,笑声清脆,在嘈杂的土嗨电音中,特别清晰地传进了步重华的耳朵,让他在一边有些不知所措。
笑够了,收声,吴雩慵懒地趴在桌子上,侧着头,自下而上地看着步重华,眼中带笑:“我卖艺不卖身的。”
又被蛊住了。步重华顺着他的话,问:“那你卖什麽艺?”
吴雩愣了一瞬,而后直起身子,附身凑近步重华。他穿着宽松的白t,露出的脖颈白皙修长,衣领在锁骨那儿露出一道暧昧的弧线。
步重华视线不知该放到哪儿去,只能胡乱的定在烟灰缸里吴雩抽过的那半支烟。他听见吴雩附在他耳边,低声说:“我卖杀人的手艺。”
说完,吴雩又笑了起来,软塌塌地靠着椅子,看着步重华笑,有些挑衅地问道:“怎麽样小警察,还买我吗?”
—
自那晚之后,步重华就记住了自己隔壁那个名叫吴雩的男人。
是哪一篇小说说过?所有的爱都有,即使那个像火柴的前端那样脆弱而微小。直到那天之前,步重华都算是过一天是一天。他好比是在一条薄冰覆盖,简直可以说没有能见度的公路上驾驶的汽车司机,必须避免往后看。
自小时候噩梦般的一个夜晚,自那场火灾之后,步重华的人生就驶上了一座过于狭窄的桥,不可能向后转。只要往后视镜看一眼,就会头晕得要命。
周末过去,他在上班的时候也会时不时想起那个夜晚的吴雩。那麽暧昧,那麽诱惑,说出来的话仿佛带着鈎子,往人的心尖上鈎。看人的眼睛却又那麽清澈,单纯得好似不谙世事。
步重华想了很多,头牌,点人,卖艺卖身……一剎那间他突然发现,有那麽多话语,那麽多的场景,将在他的记忆里,犹如远方闪烁的星星那样熠熠发亮。而这些记忆在随着他的离去而消失之前,并没有透露出它们的秘密。一想到吴雩也会这样,始终是一个谜的时候,他便感到心里空落落的。
因此,他在接下来的的日子里,每日下班都会去酒吧喝上一杯,和老板也混熟了。
酒吧老板是个很漂亮的女人,长发红裙,身姿婀娜,手边夹着一根烟,开口的声音沙哑慵懒:“你说吴雩啊,他也不是每天都来。大概是两个月前,他搬来这里,才会时不时来喝一杯。”
“那他是做什麽的?”步重华手里拿着一杯威士忌,靠着吧台随意问道。仿佛只是顺口提起了这麽一个人,绝对没有其他心思。
老板沉默了一瞬,稍加严肃道:“具体的我不太清楚,只不过我看见他和一帮不太好惹的人走在一起过,那帮人看起来很尊敬他。”
她吸了一口烟,转头看着步重华,朝着他呼出一口气:“小警察,千万不要喜欢不该喜欢的人。”
步重华立即擡眼,反驳道:“我没有。”
“好吧,你没有。”老板暧昧一笑,“那这杯酒我请了。”
酒吧几次落空后,他开始调整作息,尽量晚睡早起,但也依旧没有捕捉到吴雩有任何出入201的声响。
白天上班时,他在办公室油条们打量的视线中,顶着眼底的黑眼圈,坐在角落有些恍惚地想,吴雩真是一个古怪的人,所经之处好像只留下了一团迅即消散的水汽,让人捕捉不到。
实习期还有三个月。步重华连续十天都没有再见到吴雩,他已经放弃了偶遇的可能性,也接受了吴雩已经离开这座小镇的可能。顿时他觉得接下来重複的日子很可怕,而且他还得想办法要去接受,毕竟他得工作,他得为人民服务。
于是步重华心里不免问还要多久?到了没什麽时候是个头?
心里的绝望随着再一次见到吴雩而消散。那是个下雨天,上面派人在所里开了一个动员大会,大家加班到了很晚。出门时夏日骤雨突降,步重华在路上被浇了个措手不及。骑着所里的二八式埋头往住处沖刺,刚到楼下,擡眼就看见了坐着小竹椅正在屋檐下看雨的吴雩。
那一瞬间,步重华觉得天地万物都静了。他停好自行车,走过去,站在吴雩面前,看着他不说话。
吴雩依旧在看雨。过了一会,步重华蹲在他身边,轻轻地问:“你在看什麽?”
吴雩没有说话,只是觉得蹲在身旁的这个人,明明身材高大,长得也兇,怎麽说起话来这麽温柔。被雨打湿的心在此刻越发湿润,吴雩想起了记忆里那个模糊不清的妈妈。
他记得妈妈在一片罂粟丛下对着还是孩子的他说:“宝宝,你要知道,鸟可以在空气很稀薄的高度下飞过几千公里,但是在他们的手里,只要一紧握就会死掉。“
而在另一个晚上,妈妈拉着他的手,两人去山间散步,又对着他说:”可是这个世界的鸟儿永远不会停止飞行。“
拉回思绪,吴雩看着远处屋檐下那只受伤的湿漉漉的麻雀,见它迟迟飞不起来,心里自嘲:这麽弱,活该死在这场雨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