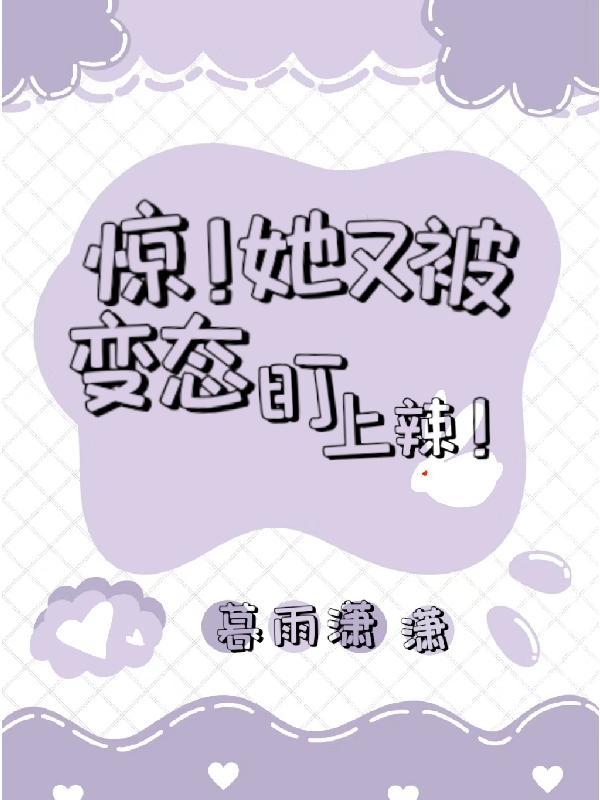笔趣小说>火葬场 np > 第248頁(第2页)
第248頁(第2页)
江益渠皺眉:「慎用!不勞而獲實非長遠之路!」
「當年洒家不就是這般灌上來的?」余東羿直愣愣的坐著也累,乾脆把後腦勺往師尊大腿上一趟,橫下身子翹起二郎腿,看見江益渠欲言又止,又眯眯眼道,「我知道,師尊您穩紮穩打,不用半點靈丹靠自個兒修煉,徒兒自然也應該多多學習。」
江益渠低頭看已經把腦袋擺進他懷裡的傢伙,不由無奈地道:「起來坐直了,青天白日,像不像話?」
余東羿可不聽話,只仰頭凝視著江益渠的眼睛:「師尊醒來為何不找徒兒說話?若不是徒兒自個兒找上門來,師尊是不是也不會再理我了?」
江益渠一愣,略微有些心虛道:「不是……」
余東羿手臂一抬,手掌摁著江益渠的後腦勺往下,腰一挺就上去吻了一口。
吻完才問:「在怕什麼?嗯?」
江益渠呼吸略微急促了些:「你……放開,為師要修煉了。」
未曾想江益渠推攮了一陣,人沒推開,反倒是胸前的衣襟散了。
余東羿得寸進尺地說:「掙扎也無用,咱倆如今都成了凡人,師尊神識高些,卻又捨不得用神識刺我,倒不如老實交代。」
余東羿一大坨地扒拉到他身上,江益渠怕他摔到地上磕著後腦勺,又要分心揪住衣領抵擋作亂的手指,不由手腳忙亂了些。
江益渠顧左右而言他道:「你有時間在這兒戲弄本座,不如趁早培元固本,鍊氣築基,以免壽數不足……」
余東羿突兀地打斷他道:「師尊可有怨懟?」
江益渠愣了愣:「何出此言?」
余東羿道:「若渡劫前您能融了分神,神魂完整,說不定便能抵擋住那最後一道……」
江益渠心神一震,正色道:「事情已成定局,沒必要做這般假設。」
余東羿依依不饒繼續道:「是徒兒阻撓您,您才放過殷幼一碼。烽火北被鳩占鵲巢,玄清宗納的弟子不出一個月便如鳥獸般散了,轉眼間天下大變,若要怪誰害您淪落到此番境地,師尊便來怪我吧。」
江益渠皺眉道:「渡劫之事乃為師一意孤行,終究是急躁了些,本座自作自受,你也大可不必這般把擔子往自己身上攔,那狐狸……也是本座決定要放過的。」
余東羿笑了:「這麼說,您肯容得殷幼在此處陪陪徒兒了?」
江益渠愈發不悅道:「此事另當別論。」
「哎——」余東羿拉長了音,開始攪和著不許師尊修煉了,攀附著親上江益渠的脖頸,又翻過來反客為主把人壓在身下,「有隻狐狸作陪有何不好的?先不說徒兒身體不好得靠殷幼日日放血吊著,師尊您重修煉整日呆在屋裡忙不贏陪我,叫徒兒如何是好?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