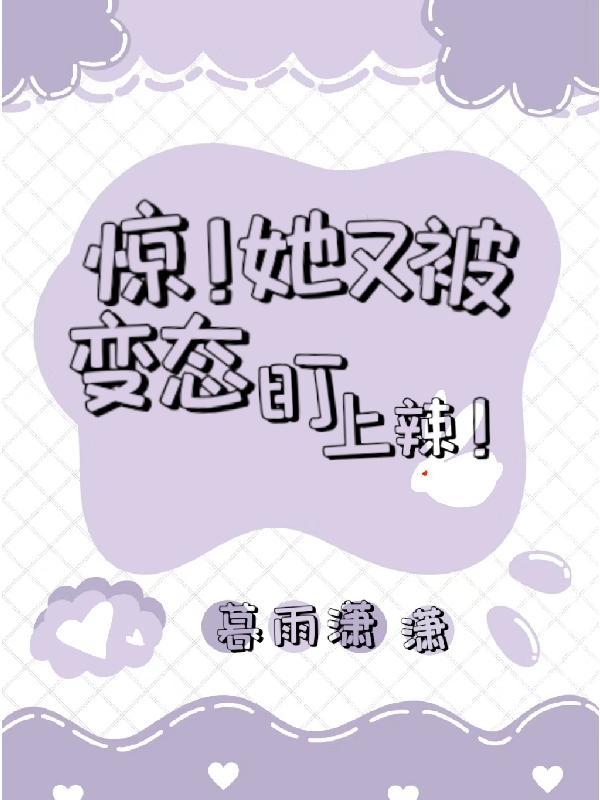笔趣小说>偏航变桨齿轮箱 > 第91章(第2页)
第91章(第2页)
雨依旧很大,她的后背湿透瞭,但鬱理感觉不到冷。
须云山传来清啸辽远的风声,仿如为瞭这片墓园吊唁的呜咽。
她看著许梦昕的脸,她还是无论何时何地提起来都是令人惋惜的年纪,她还有梦想,还有出国深造的机会,她还有无数的可能性和幻想。
直到现在,直到三年后迟到的一束铃兰,鬱理终于可以打碎由她亲手编织的,属于薛定谔的梦境。
隻要她不来,许梦昕就不会死。
太傻瞭。这种小孩子也不屑的逃避。
无孔不入的雨水洇下来,正正切过女孩微笑著的照片。鬱理把剩下的纸巾团在手裡,不厌其烦地擦拭水迹。
如果不是看到她的遗照,鬱理不会惊异,自己竟然记得那麽多有关她的细节。
明明已经过去很久,那些为数不多的回忆,就和一个主人搬走的旧房子,所有傢居盖上一层白色的遮灰佈,被留下的所有事物扫过一层朦胧的雾,什麽也看不清。
但她记得这个温吞如水的女孩子,她说自己真的喜欢庄铭,但同时,清醒地知道庄铭不会永远和自己在一起。理瞧不上她骨子裡对自己的轻慢,同时对庄铭的厌烦更上一层。
庄铭那种垃圾,凭什麽配得上这样美好的爱?许梦昕真是傻子,她后来怎麽又喜欢周敬航,她还不如喜欢自己算瞭。
那时候的鬱理赌著气,没意识到自己把这句话说出口,她后知后觉地,听到许梦昕的回答。
“嗯,我最喜欢你。”她歪著脸,阳光洒在她的睫毛和下唇,像窄口瓶储存的金色蜂蜜,她有著山水画的五官,线条很淡,却很柔美。
“你是我最好的朋友,鬱理。”
鬱理没有反驳小女生天真浪漫的猜想,她愿意接受这份不对等的感情,直到某天有个陌生号码给她发来许梦昕和周敬航的合影,和一段语焉不详的录音。
她不会用动物去形容许梦昕,她其实不是很温驯,也没有特别乖巧。她像冰冻三尺的长冷湖面,看著冰冻沉寂,如果贴著冰面去听,其实能听到最深处缓慢流动的源流。
她一边说著,救我,帮帮我;一边又说,可不可以把周敬航让给我。
当时为什麽要说谎呢?许梦昕。
鬱理没告诉别人,她在许梦昕去世一年后,患上瞭较为严重的失眠症,她不再能轻松入睡,那段时间,烟抽得尤其凶,工作滞后半年,迷上全球各地飞著赌钱。
山一样的筹码潇洒地推出去,隻玩运气类的游戏,有时候运气很好,有时候运气很差,有时候迷瞭眼,摘掉手指的古董钻戒当做玩具扔到衆人面前。大傢起哄地笑,视线天旋地转,闭上眼隻有黄金钻石珠宝,和公海上恣意放肆的大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