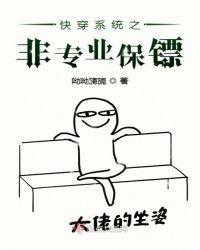笔趣小说>喜相逢集团有限公司 > 第30节(第3页)
第30节(第3页)
傅玉行有种直觉,这人是个疯子。
只不知为什么,这疯子找上了他。
“二少爷怎么不喝呀?”他眼神里既有极端的疯,又有极端的冷静,忽然懂了什么,笑起来,“这锅粥里没有毒了,我那么做也全是为了保护你呀!否则你早就已经死在张广刀下了。”甚至还有着那种疯子的敏锐。
傅玉行道:“你到底是什么人,想干什么?”
驼子对他的话仿佛充耳不闻,语气始终是絮絮的,自言自语,“你放心,二少爷,我是不会让你出事的。”
“……”
“二少爷,你真的一口都不吃吗?真的不吃吗?”
傅玉行不说话。
驼子被他盯得只得慢慢缩回了手,也慢慢变了一副脸色。
“也是,也是……我们吃的这些东西你毕竟是看不起的。”他整个人好像忽然缩得很小,很自卑,很悲伤。
傅玉行觉得他那样子有些像一个人,一个遥远又陌生的印子在他脑子里像墨迹渗纸一样慢慢透出来。
驼子还在喃喃自语:“我知道你看不上我,我们这种人永远都入不了你的眼。”
我们,我们?
“你是生下来什么都有的人了。你一句话就可以杀一个人。”
“可是二少爷,我就那么一个弟弟。”
傅玉行感觉到不对,因为他猜出眼前这个人是谁了。
虎逃山那天之后,整个傅家一直惨惨淡淡,笼罩在一片阴影当中。
州府仍然每天派出差役搜山,但全无消息。宣州街头巷尾早已传开,傅家不知是得罪了什么人,二少爷遭人绑了,生死不明,八成已经没戏了。
敬斋听说他们从茅店里只挖回来几具尸体,一开始还沉默不语,要躺下时忽然吐了一大口血。
芳仪倒是没有再倒下,她一反常态,什么也不问,什么也不打听,只是每天下厨做饭做汤,凉了,又重新做过,好像生命里只剩下这一件事情,循环往复,谁劝也不听。“玉行在外这么久一定饿坏了,等他回来了,总得有一顿热饭吃。”
赵蘅这时已无力主持大局,那天之后,不知是她还是腹中胎儿受了惊吓,她每夜做噩梦,连着吃了几天压惊安胎的药。只有玉止每日照常主持事务,安抚二老,照顾赵蘅。
亲邻中有些心怀鬼胎的,早早便等着上门吊唁讨好处,先后不知打出去多少。更有些人,听说二少爷生死不明,索性假装劫犯,写了勒索信送到傅家门口,要求傅家将银子若干埋到某某路口某某树下云云。有时信送到二老那里,又惹的两个老人大受刺激。
直到第三天晚上,一封石头压着的纸条安安静静出现在台阶上,像一次客气的叨扰,不惊动任何人。
薛总管本以为又是一封闲人伪装的勒索信,真正打开一看,却大惊失色,一路急匆匆送到栖风院里。
当天夜里,整个栖风院死一般的寂静。
赵蘅坐在床上,一只手习惯性放在小腹上,视线却直直望着屋中另一头的玉止。
当那张用血写成的字条出现的第一眼,他们就知道,就是这个人了。
血淋淋的纸面上只有寥寥数字:明日巳时,城隍庙。再有官兵,他性命不保。
字迹潦草,没有落款,也没有指名道姓,但写信的和看信的都心领神会。
赵蘅想了又想,想了又想,还是道:“玉止,你别去了,我好怕。”
从她看到那张字条开始,就有一种强烈的不安萦绕心头。也许她敏感,也许她多疑,也许怀孕让人变得脆弱小心翼翼,可那种心悸感就是无法消除。
“阿蘅……”玉止没有马上反驳,神情里却全是欲言无声。
赵蘅光着脚从床上下来,半是安慰半是乞求道:“我们可以慢慢想办法,总有办法把人救回来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