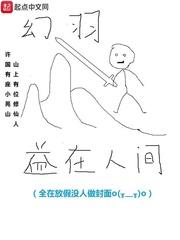笔趣小说>飘飘雏几级进化 > 第97章(第2页)
第97章(第2页)
她懂,她懂这种感受,甚至能用文字描述,陶浸消失在她生活中时,她的爱情也死掉了,后来那个人便出现在梦里,说“飘飘你过来”“冷不冷”“又快要下雪了”。
那次陈飘飘醒来,很执拗地去找雪地靴,在鞋柜里翻啊翻,想会不会搬家的时候不小心扔掉了,她跪在地上,甚至毫无常识地趴下去,往缝里找。
她坐在地上努力回想,头发和睡衣都很乱,像一只露出芯子的布娃娃。
最后是从衣柜的上层找到的,包起来了,和她买到的第一只爱马仕放在一起。
陈飘飘拿出来,穿上,拎着单薄的睡裙走两步,不伦不类,热得烘脚,而且也小了,指甲顶得难受。
也没有长胖啊,怎么会脚变大了呢?还是说鞋子放久了会缩水?
陈飘飘躺在沙发上,搜了一晚上雪地靴久不穿会不会变小。
她怎么会不懂那种如梦初醒的感受呢?回忆比雪地靴更夹脚,顶得人想要痛哭出声。
她会有合脚的雪地靴,更精致的,更漂亮的,更昂贵的,可她再也没有陶浸了,她和女主角一样,永远失去了她的爱人。
她微微哽咽,酸楚在心里蔓延,然而她的情绪很诡异,七情六欲像在猫砂里,迅速凝结成团,变为无色无味的干燥形状。
“要不要放点音乐?”fay悄悄找陶浸。
陶浸在陈飘飘呼吸的间隙里轻声问:“需要吗?”
“不用。”陈飘飘望着剧本,把耳发勾上去。
她在尴尬,真神奇,当着陶浸做那种事时都没这种被凝视的赤裸感。她陡然意识到,自己在表演上,对陶浸,一直心虚。
她总觉得陶浸高人一等,或许真正原因是,连陈飘飘自己都认为,陶浸长成了她们从前所期盼的那个大人,而自己并没有。
越想眼眶越干涩,她放下剧本,无奈地笑:“对不起,我哭不出来。”
剧场呼吸可闻,所有人都没说话,舞美设计站在座位旁边修图,fay戴着耳机挑选合适的音乐,按部就班得仿佛台上没有出状况,同事们将解决问题的时间交给几位核心人物。
吴老师对陈飘飘招手:“来,你过来。”
陈飘飘听话上前,蹲到舞台边,吴老师缓声道:“我再给你讲一遍戏,从这个人物内在出发,咱们先把情感捋顺了,有时候吧,我们说感情脉络就跟水龙头似的,疏通了,它自然而然就出来了对不对?你要是刻意去拧,那没用,越拧越干。”
她拍拍陈飘飘的胳膊,看剧本:“没关系,啊,还有时间,先调整调整。”
陈飘飘抿嘴,点头,认真听吴老师讲。
她们前后翻着书页,十来分钟后,陈飘飘说,想再试一下。站起身回到舞台侧面,先在道具床上酝酿片刻,音响里传来丧钟般的嗡鸣,陈飘飘猛地坐起来,空洞地苍白地望着虚空中的某一点,音乐戛然而止,灯光打得阴阳相隔。
呼吸,急促的呼吸,缓慢的呼吸,胸口咽血一缩。
眼泪该出来了,可陈飘飘眨了眨眼,一口气松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