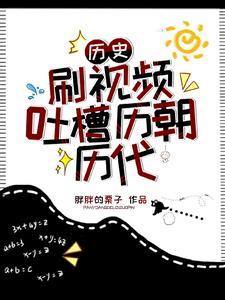笔趣小说>婚礼当天我把老婆送给她的白月光 > 第7章 走去撸串儿(第2页)
第7章 走去撸串儿(第2页)
算一算,我俩也吃遍了大半个城。
我从来都不主动去想以前的事,因为我觉得,就算现在过得再累,至少在家呆着就是安全的。不像小时候,睡着觉会突然被我爸薅起来抽。没理由,打老婆孩子需要什么理由?
这两冷,烧烤店里没什么人。
我俩到最里面的卡座里坐着,老板娘过来扔下菜单,让我俩自己划对勾,回去给我俩搬小太阳。
梁墨冬趴在桌上,扶着额头,一边画勾一边问:“白的还是啤的?”
啤的胀肚,我说:“白的。”
他把车钥匙丢过来:“后座有两瓶茅台。”
“咱俩走着来的。”我说:“你喝多了吧。”
他打开钱夹,抽了几百块钱给老板娘,叫她去买瓶青花,并且把菜单递给她:“记得上盘咸菜。要那个……”他捂了一下脸,很明显真喝大了。
“萝卜条是吧?”老板娘接上,“我认得这小姑娘,以前老来,每回都吃这个。”
说罢朝我笑了一下,转身走了。
随着小太阳渐渐燃起,我的手脚也渐渐暖了起来。
老板娘买来白酒时顺便给梁墨冬拿了包湿巾,他擦了一把脸之后,又呆坐了一会儿,神情才爽利了些。
我打开酒瓶,屋子里顿时多了一股酒香。
见梁墨冬把酒杯也摆了过来,便说:“不给你倒了,你已经不行了。”
“没事。”他还挺执着,“还没跟你喝过酒。”
行吧。
还真是没跟他喝过。
我倒给他,一边找点话题闲扯:“你怎么老喝成这样?”
他端走酒杯,瞥了我一眼:“你好意思说我?”
我用酒杯碰了碰他的,说:“我那是工作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