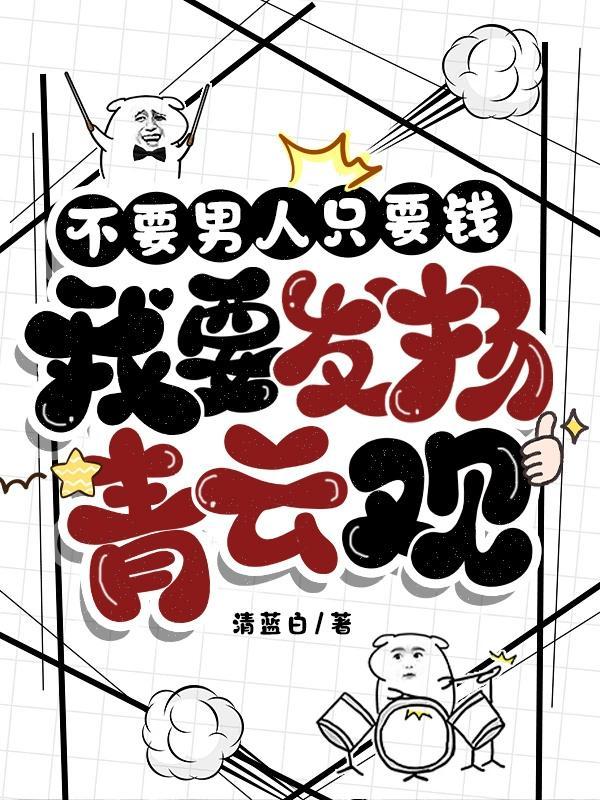笔趣小说>被迫成为太子宠臣76章 > 第14頁(第1页)
第14頁(第1页)
牧野撐開眼皮,看到他舉到面前的詔令,輕輕「嗯」了一聲。
「今年冬季圍獵,聖上命我隨行。」
承帝三年未詔過她,今年不知是何意。
許是南方倭寇作亂,朝廷連派兩次兵都未能收復丟掉的城,現在想起她來了。
裴辭沉吟不語。
承帝忌憚牧野,將她視為凌駕於皇權之上的刀。
就算承帝受局勢所迫,給了牧野兵權,等這把刀用完了,又要想著收場。
牧野的聲望在民間蓋過了皇家權威,燕北尤甚,只知牧野大將軍,不知當今聖上為何人。
兩次用之棄之,就算牧野無所謂,但擋不住民間不滿,承帝沽名釣譽,自是不允許出現那樣的局面。
裴辭想到的,牧野也想到了。
但她還是要去,因牧氏家訓——
忠君報國。
不管這個君是什麼君,牧野都要服從,她不能辱沒了牧家三代,不能讓長輩們的犧牲成為笑話。
更重要的是她既有能力護住百姓,就一定要護。
裴辭知道眼前的人,就只是牧野了,乾淨正直的牧野。
他的神色複雜。
「我與你一起去。」裴辭說,「萬一受了傷還有我在。」
牧野往床塌里又挪了挪,調整了一個更舒服的睡姿。
「算了,奉鏞都城裡的那幫鼠輩,還沒有人能讓我受傷。」
裴辭深深凝著她,半晌,幽幽道:「未必。」
牧野閉著眼睛,笑了笑,沒在意。
「我多獵幾隻白狐,帶回來給先生做裘衣。」
順便找個機會,要把太子廢了,她的腦袋疼死了,此仇不報非君子。
裴辭坐到塌上,離她更近。
「你要一個人去,戴好面具。」
牧野困極了,裴辭又一直在她耳邊說話,她伸手,捂住他的唇。
「先生好囉嗦。」
牧野沒有像在白日裡習慣性的壓低嗓音說話,此時的聲音攜了三分柔軟溫存。
裴辭呼吸一滯,握住她的手腕,藏在衣袖裡的腕子,是那樣纖細,他忍不住攥緊了。
牧野已經睡沉,手自然垂了下去,感受不到那逼迫人的力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