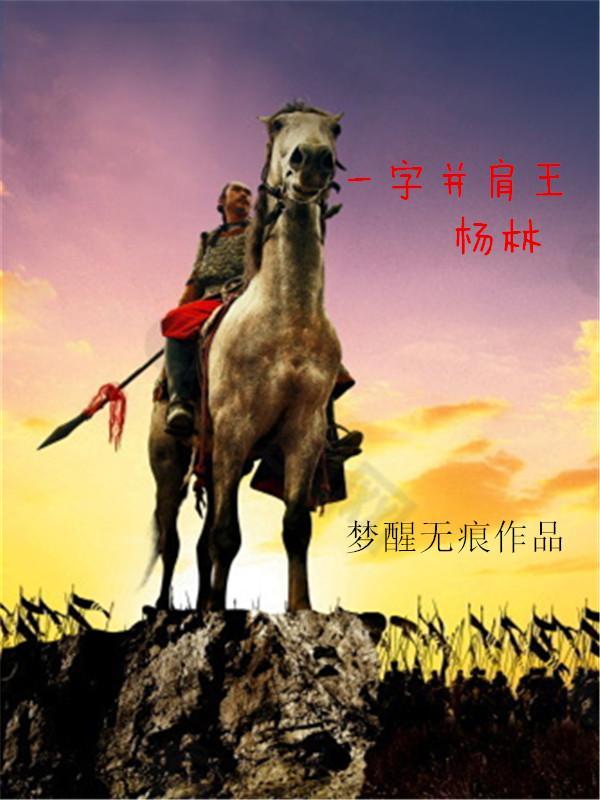笔趣小说>非人类饲养员解说 > 第318章 祭祀与新娘(第1页)
第318章 祭祀与新娘(第1页)
为了缓解这种暴风骤雨般的痛苦,喻清大口大口的吞噬药片,已经出了医嘱和处方上的限制剂量,在此之后,过量的药剂产生作用,他像木偶一样坐在房间里。
静坐到现在,终于像通电的老旧机械一样,缓慢而僵硬地转动脖颈。
他拧开了瓶盖,将虫子倒进已经枯萎的鳟鱼海棠花盆里,用土把它们埋了起来。
玻璃瓶的瓶口有一丝微不可察的干涸血液。
喻清注意到了那一丝暗红色,眨了眨眼,这才回忆起来,她在捉这些萤火虫的时候,似乎被荆棘割破了手。
是她的血。
他下意识抬手摸了摸,那些血液竟然还泛着一缕湿润。
没干?
他有些反应不过来。
也不知道,在这一刻,他身体里正在上演着一场悄然的异变。
某个瞬间,喻清猛地颤动了一下,感觉有什么与自己从体自己体内割裂出来。
他浑身冷,难以抑制地颤抖起来,弓着身体抱住自己的肩膀,像骤然掉进了极寒之地。可随后大脑的眩晕像有人把他的头摁进了正在高旋转的洗衣机里,晃到他几乎快要失去意识。
尖锐的疼痛蔓延进四肢百骸,像要生生把他的皮肉与骨骼用利器割开,他有一种被撕扯的疼痛感。
可仔细感受,却现,这种疼痛并非来自于**,而是灵魂,又或者是更加虚无缥缈的东西。
从某个维度来说,他在这一刻被割裂了,又或者说在这一刻迎来了某种意义上的生,只不过当下的喻清什么都不知道,他懵懂到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。
脑海中甚至产生了甚至出现了许多与自己人生毫不相干的记忆碎片,那些画面像坏掉的走马灯一样飞旋转,随后消失湮灭。
窗外的光影不断变换,斗转星移,又是一天。
“咔嚓”一声,玻璃碎裂的声音在空荡的房间响起。
他在这一瞬间清醒了过来。
仿佛第一次苏醒,喻清的眼神显得有些懵懂,宛如一只生的动物,睁开眼,茫然地看着碎掉的玻璃瓶。
某种意义上,这是诞生的时刻。
他捡起玻璃碎片,浑浑噩噩地走回城市。
写字楼外光洁干净的玻璃倒映出他的模样。
喻清现自己忘了戴帽子,抬手将帽兜罩在头上,再一次面向镜子时,有一瞬间在镜子里看到了另外一张脸。
他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有些陌生?
而下一秒,这张陌生的脸和记忆中的样子融合了。
他揉了揉眼睛,有些茫然。
“喻先生。”
背后忽然传来了一声问候。
声音冰冷,没有温度。
喻清回过头,现身后不知什么时候站了几个身着长袍的诡异信徒。